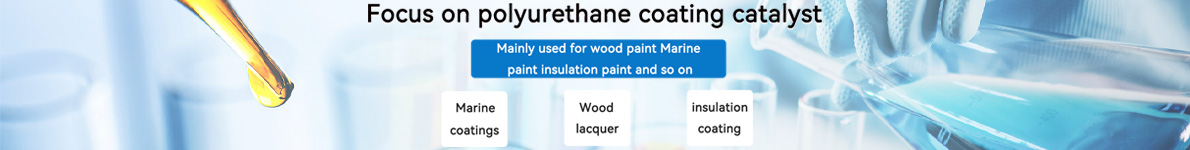广州有一种以玻璃油画为装饰的家具,这其中以屏类家具为常见。玻璃油画就是在玻璃上画的油彩画,于清代初期由欧州传入中国。它首先在广州兴起,并形成专业生产。与一般绘画画法不同,玻璃油画是用油彩直接在玻璃的背面作画,而画面却在正面。其画法是先画近景,后画远景,用远景压近景。尤其是人物的五官,要画得气韵生动,就更不容易了。 清代的“玻璃”,是指从欧洲进口的玻璃产品,或者是指造办处“玻璃厂”等作坊仿照欧洲技术制造的玻璃。传统本土技术制造的玻璃产品,则呼之为料器、琉璃。 乾隆时期负责玻璃厂的法国教士汤执中编写有《法汉词典》,今天译为“玻璃”的glass,在该词典中却被对译为“琉璃”;crystal一词,才被译为“玻璃”。而crystal一词,在欧洲语言中,是指天然水晶,在今天汉语中译作“水晶玻璃”或“晶状玻璃”。 由于玻璃的光透度、明亮度和使用效果均佳,渐渐地由外檐过渡到内檐使用,室内装修隔扇上也开始用玻璃镶嵌隔扇芯。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辑)·雍正朝》(以下简称“辑览”)一书中屡屡出现清代宫廷中使用玻璃的信息,甚至,雍正本人对于这已西洋舶来品的强烈兴趣在档案记录中也清楚留痕。 伴随玻璃的传入和统治阶层的广泛使用,随之而来的就是玻璃油画业的兴起。 18世纪时,耶稣会士郎世宁学习在玻璃和绢上作画,得到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恩宠,受皇帝的亲自委托绘制玻璃油画。 早期玻璃油画主要用于王宫建筑的装饰上。由于玻璃油油画色彩鲜明强烈,强烈的装饰效果,进入到了清代宫廷中,成为当时皇家贵族所追求的时尚。 十八世纪玻璃油画在欧洲被称为背画(Back Painting),即“这种绘画与在画布和木板上绘制的画完全相反,它在玻璃背面完成,而在正面可以清晰地看见”。 玻璃油画早见于十五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圣像画。由于绘制技术难以掌握,到十八世纪欧洲已经不再流行。 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广州口岸,玻璃油画却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广州画匠外销画的重要画种。 当时一位叫做德经(De Guigue)的西方人在其游记中称广州为中国的玻璃油画中心,并记载了广州玻璃油画的具体绘制方式:中国画家喜欢用薄的玻璃镜作画板,因为厚的玻璃镜会使颜色变浅,影响画面效果。他们一般用油彩绘制,有时也用树胶混合颜料作画,绘制时画家先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一种特殊的钢制工具将镜背面相应部分的锡和水银除去,以便划出一块清晰的镜面来绘制图案。 广州生产的玻璃油画的题材多是应欧洲 “中国趣味”的需要而产生的,题材多取自自然风景、花鸟和吉祥如意图案,另一部分受西方绘画影响,画有西方建筑、车、船和人物。 随着玻璃画工艺在中国的盛行,除了大部分外销之外,很快这种来自西洋的装饰技术开始应用于家具制作,特别是在屏风类家具上应用广泛。 从造办处的活计文件记载上我们看到雍正时期所作的屏风有一半以上都带有玻璃镶嵌。 “广东粤海监督监察御史”祖秉圭呈进了大片的平板玻璃片,除此之外他还呈进了一架带有楠木座的“玻璃插屏”。 在“辑览”一书可以感受到这类玻璃插屏作为一种时新摆设,一时间很受青睐。 雍正三年(1725年)木作档案中就有“再将所有的大小玻璃插屏俱查出来”的指令,同时,甚至有这样的记录: 玻璃插屏一座,着粘补见新,玻璃有损破处俱做竹节式合牌遮挡,钦此。 玻璃插屏上的玻璃片如果有磕损,居然并不是拆下来再换上新片,而是利用工艺手段加以遮挡。由此,可见水晶玻璃在当时的珍贵程度。 历史上广东粤海监督监察御史真的曾经向皇帝进献过玻璃围屏二架,每架十二扇,合计二十四扇! 这种利用欧洲进口透明玻璃、在广州加工而成的时新奢侈品,被千里迢迢献宝一般进呈给皇上,可见其贵重程度非同一般。 围屏自然是落地式,尺寸巨大,而且多达十二扇,屏面镶有玻璃,其运输难度可想而知。 此后,乾隆时期因乾隆帝钟爱紫檀,而又有紫檀镶画玻璃炕屏进贡宫中的记载。 在清代宫中,现在还有不少镶嵌以玻璃油画的广式风格家具。它们无一不是工精料细、富丽奢华,深受清代帝王推崇。 不过到了乾隆后期,可能是因为玻璃的取得愈来愈容易,这种屏风不再像之前一样流行,导致乾隆皇帝在二十年后屡屡下旨。将之前家具上镶有的玻璃取下,换成紫檀木板,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传世例子如此之少的原因。 伴随清朝的衰亡,玻璃画开始走向衰败,这种逐渐消失而成为全世界的绘画,占据了清代绘画史值得研究的一页。